日期:2025-09-03 04:40:0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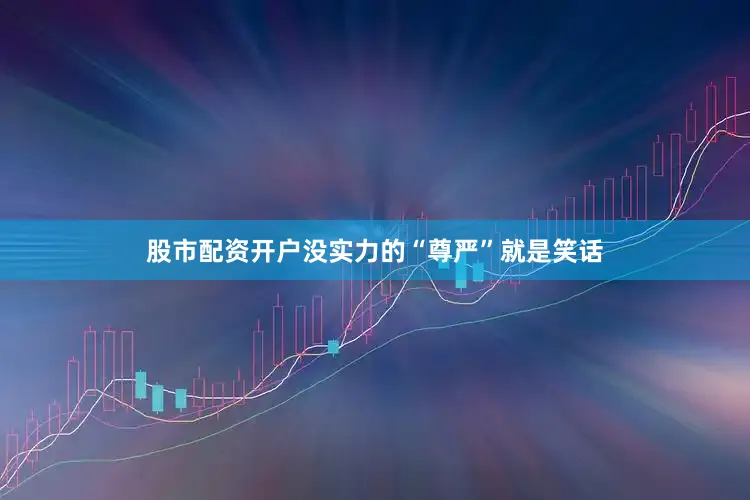
细品《金瓶梅》,笑解风月事,精华部分不删减!点“关注”,不迷路,您懂的。。。
细品《金瓶梅》,笑解风月事,精华部分不删减!点“关注”,不迷路,您懂的。。。
《金瓶梅》一书真是毒辣,它不写英雄好汉的高光,专描凡人俗子的窘迫;不赞顶天立地的豪情,偏揭“窝囊”背后的人心与世情。
书中武大郎、蒋竹山、花子虚三个角色,都顶着“窝囊”的名头,却藏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活法。
武大郎是“糊涂人拎不清,硬拿鸡蛋碰石头”,蒋竹山是“穷书生有傲骨,落难也不折腰杆”,花子虚则是“软骨头任人宰,被掏空了也不敢哼一声”。
这三种“窝囊”,恰似三面镜子,照见了末世里小人物在强权、欲望、背叛中的挣扎与沉沦。
武大郎:糊涂争“尊严”,狠话引杀身
展开剩余86%武大郎的悲剧,从来不是“没力气反抗”,而是“没脑子认不清局势”。
我们且想一想,他“身不满五尺,面目丑陋,头脑浊蠢”(原著语),靠着巷口卖炊饼糊口,偏娶了潘金莲这般“容貌出众,水性杨花”的妇人。
这本就是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的失衡,他却偏要在“丈夫尊严”上争强好胜,到头来把自己逼进了死局。
那日他撞破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私情,不寻思“武松远在阳谷县,自己敌不过西门庆”的现实,反倒在郓哥的撺掇下冲进王婆家,对着潘金莲吼出“你若不依,等我兄弟武松回来,定不饶你,须教你剥皮抽筋”的狠话。
这话听着解气,实则是“自寻死路”——他忘了,西门庆是清河县里“有钱有势,专好结交官宦”的主儿,潘金莲早已对他“厌弃至极,只盼他早死”,这番狠话,不过是给了那对男女“灭口”的理由。
果不其然,潘金莲听了这话,“心下慌了,便与西门庆、王婆商议,定了毒计”,最后一碗砒霜,让他“七窍流血,呜呼哀哉”(原著语)。
看官细想,武大郎的“窝囊”,藏在“糊涂”二字里。
他以为“丈夫”的名分就能换尊严,以为“兄弟武松”的名头就能吓退恶人,却不知在清河县的“强权逻辑”里,没实力的“尊严”就是笑话,没靠山的“狠话”就是催命符。
作者兰陵笑笑生骂他“头脑浊蠢”,真是一针见血——他不是“可怜”,是“愚蠢”:明明可以暂时隐忍,等武松回来再做计较,偏要逞一时口舌之快,把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。
这般“窝囊”,是“自毁式的糊涂”,让人叹息,却不值得同情。
蒋竹山:窘迫守“体面”,挨打不折腰
蒋竹山的“窝囊”,最是特别——他穷、他输、他被李瓶儿骂“银样镴枪头”,却半点没有“窝囊”的底色,反倒藏着几分“穷书生的硬气”。
他本是“东京来的医生,在县前开了个药铺,人材也有几分斯文”(原著意),没钱没势,却敢跟西门庆抢女人,这份胆量,就比武大郎、花子虚强上百倍。
那日李瓶儿被西门庆“哄得心动,却还没定下名分”,加上西门庆因东京亲家出事而爽了与李瓶儿的婚约,被蒋竹山趁虚而入。
他不像西门庆那般用钱财诱惑,只凭着“会说软话,懂女人心思”,日日陪着李瓶儿说话解闷,竟让李瓶儿“改了主意,愿嫁与他”(原著语)。
这事戳了西门庆的肺管子,没过几日,东京事了,就派“两个光棍,把蒋竹山拖到巷口,一顿好打,打得他头破血流,还逼他写下退婚书”(原文意)。
换作旁人,怕是早就跪地求饶,求西门庆“饶命”,可蒋竹山呢?
他“收拾了药铺的家当,雇了个驴车,悄没声儿离开了清河县”——没求饶,没抱怨,更没回头找李瓶儿纠缠,虽输了婚事,挨了打,却保住了最后的体面。
他唯一的“丢人处”,是婚后“在夫妻之事上力不从心”,被李瓶儿骂作“死王八,银样镴枪头,中看不中用”(原著语)。
可看官须知,这是生理上的窘迫,不是人格上的懦弱。他敢“虎口夺食”,是因为他不信“西门庆能霸占所有女人”;他敢“挨打后走人”,是因为他不愿“在强权面前弯下腰”。
这般“窝囊”,是“处境所迫的无奈”,不是“心甘情愿的顺从”。
比起武大郎的糊涂、花子虚的麻木,蒋竹山的“窝囊”里,倒藏着几分凡人的傲骨——哪怕穷到吃不上饭,也不愿丢了做人的底线。
花子虚:麻木任“宰割”,窝囊到死休
若说武大郎的“窝囊”是糊涂,蒋竹山的“窝囊”是无奈,那花子虚的“窝囊”,便是“刻在骨子里的麻木与顺从”,是“被人掏空了家产、抢走了老婆,却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”的悲哀,堪称《金瓶梅》里“窝囊天花板”。
他本是“花太监的亲侄子,继承了万贯家财,住在清河县的大宅院,娶了李瓶儿这般貌美的妇人”(原著意),日子本该滋润,却偏要跟西门庆拜把子,加入那“十兄弟会”——一群“表面称兄道弟,实则互相利用的酒肉朋友”。
西门庆早就对李瓶儿“垂涎三尺”,可花子虚呢?把西门庆当成“铁哥们”,任由他“日日出入自家宅院,与李瓶儿眉来眼去”,连丫鬟都看在眼里,他却浑然不觉。
更荒唐的是,李瓶儿为了方便与西门庆私会,竟把自己的丫鬟迎春“送给西门庆伺候”(原文意)——这等“引狼入室”的事,花子虚竟当是“兄弟间的情分”,连半点疑心都没有。
最让人憋闷的,是李瓶儿转移家产的事。
她趁着深夜,“把家里的金银细软、古董字画、现银箱子,一箱箱搬到西门庆家”(原著意),从头上的金簪到床底的银子,搬得一干二净,花子虚却像个“局外人”,连半点风声都没听到。
直到他因“家族财产纠纷”被抓进大牢,李瓶儿用他的银子托西门庆“打点关系”,把他捞了出来。
他刚出狱,见箱子里的三千两银子没了,才敢“小心翼翼地问李瓶儿:‘银子是不是在西门庆那儿?’”(原文意)
这话一出口,平日里“温柔体贴”的李瓶儿瞬间变了脸,对着他破口大骂:“你这个蠢货!自己惹了官司蹲大牢,我一个妇道人家,求爷爷告奶奶才把你救出来,你倒好,刚出来就跟我算账?那银子是你亲笔写帖子让我用的,现在倒反过来怪我?人家帮你办事不要钱吗?你该去谢人家,不是来跟我要钱!”(原文意)
这通骂,骂得尖酸刻薄,可花子虚呢?他“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,瞬间没了声响”(原文意)。
满肚子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,全都咽回了肚子里,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。
他明明是被抢了老婆、搬空了家产,却活得像个“做错事的孩子”,连质问的勇气都没有。
没过多久,这份“窝囊气”在他心里积成了病,得了伤寒,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李瓶儿刚开始还“装模作样请了胡太医来看病”,后来嫌“花钱太多”,就断了药,任由他“在病痛里熬着”(原著意)。
他熬了二十多天,最后“眼睛都没闭上,就含恨而终”——到死都不知道,自己的老婆早就跟“好兄弟”勾搭在一起,自己的家产早就被搬空,自己不过是个“被榨干价值后丢弃的废物”。
看官试想,花子虚的“窝囊”,不是“没力气反抗”,是“没胆子反抗”;不是“没发现背叛”,是“发现了也不敢承认”。
他活在自己的“温水”里,把西门庆的“觊觎”当“兄弟情”,把李瓶儿的“背叛”当“夫妻义”,直到被煮死了,都不敢哼一声。
这般“窝囊”,是“自我放弃的麻木”,是“被背叛到一无所有的绝望”,让人看得胸口发闷——不是恨他懦弱,是疼他活得太憋屈,太不值。
结语:三种“窝囊”,一面世情镜
《金瓶梅》写这三种“窝囊”,从来不是为了“嘲笑小人物的懦弱”,而是为了“揭露末世里的生存真相”:武大郎的糊涂,是“没实力却要争不属于自己的尊严”,到头来只能被强权吞噬;蒋竹山的硬气,是“再窘迫也不丢做人的底线”,哪怕输了也能保住体面;花子虚的麻木,是“在背叛里自我麻痹,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”,最终只能被掏空、被丢弃。
这三种“窝囊”,恰似三种活法:有人糊涂地死,有人硬气地活,有人麻木地沉沦。
而清河县里的西门庆、潘金莲、李瓶儿,不过是“强权”与“欲望”的化身,他们推着这三个小人物走向不同的结局,也照见了整个末世的荒唐——当“礼义廉耻”成了摆设,当“强权压倒公理”,小人物的“窝囊”,从来不是个人的错,是时代的悲哀。
看官读到此处,当知《金瓶梅》的深刻:它不写“善恶有报”的童话,只写“人心与世情”的真实。
这三个“窝囊”的角色,不是书中的“笑话”,是现实里无数小人物的缩影——他们的挣扎与沉沦,才是《金瓶梅》最让人揪心的地方。
发布于:河南省国家认可的配资平台,融盛配资,线上股票配资专业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我要配资网平台球员此前已决定离开亚特兰大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